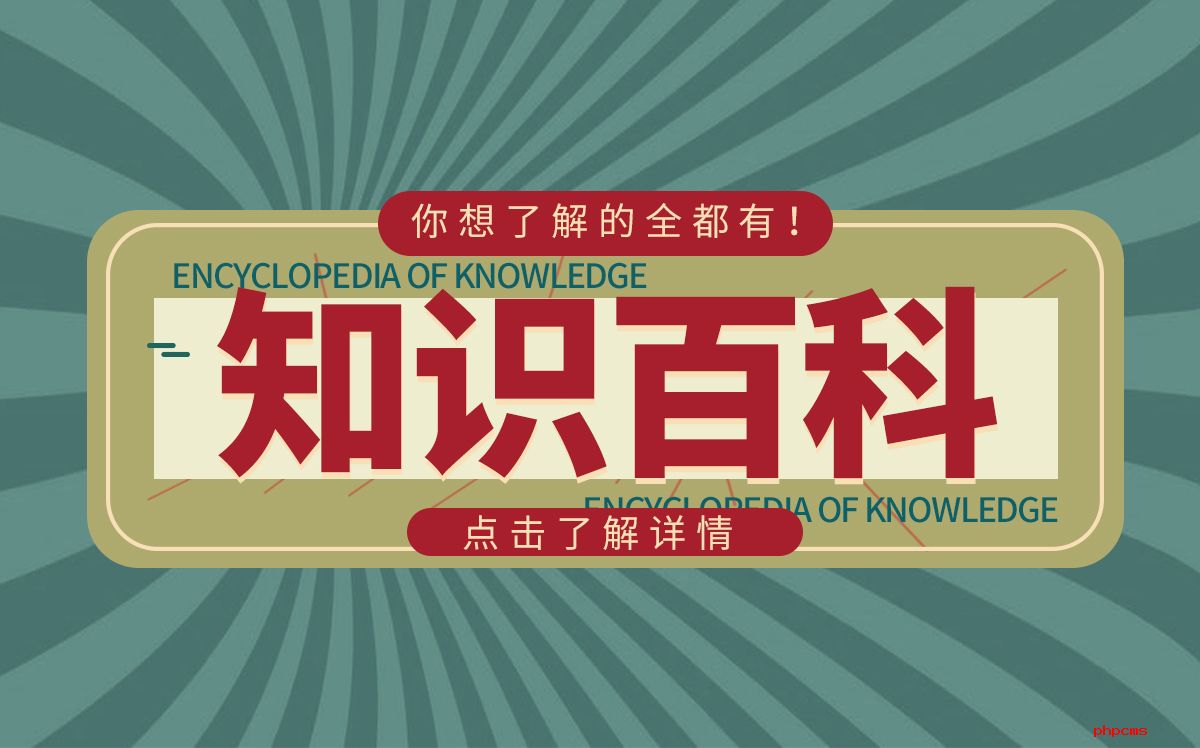5月底,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迎来了里程碑时刻。他们在官方社媒上确认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正式批准了其成立以来的首次人体临床试验,其充满科幻意味的“可穿戴脑机接口设备”将正式进入商业化流程。国内外各大媒体纷纷用“重磅”“成真”这样的大词来报道此事,那条官方公告也喜形于色:“这是与FDA密切合作所取得的难以置信的工作成果,是重要的第一步。”
与之呼应的是,Neuralink在资本市场的行情出现了同步暴涨。据媒体报道,Neuralink的老股此前一直以50亿美元的估值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等到FDA批准试验的消息曝出来,已经有卖方将估值调整为70亿美元(约合502亿元人民币),标价上涨到了每股55美元,刺激得很多生物学家、医学专家主动“跨行”呼吁投资者冷静。例如例如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心脏电生理学家Arun Sridhar就在推特上公开喊话:“这是一项用来评估安全性和耐用性的研究,在任何形式上都无法证明目前的估值是合理的。”
其实50亿的估值就很不合理了。Neuralink上一轮融资是在两年前完成的,当时他们以接近20亿美元的价格从Valor Equity Partners、Craft Ventures、DFJ Growth、Dreamers VC那里拿到了大概2.05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以50亿美元的估值计算,老员工和早期投资者们手里的股票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完成了150%的收益。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而且根据Caplight等三方平台提供的数据,实际上大约85%的pre-IPO轮公司会在二级市场出现“贬值”,平均相较于上一轮的估值规模会打折47%。股票交易在线平台Hiive的首席执行官Sim Desai最近就委婉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承认目前市场对Neuralink的股票存在着“巨大的需求”,但大部分投资者都认为45亿美元左右的估值更加合理。
可以说,Neuralink目前获得了整个赛道里“空前”的认可。不出意外,它将顺利地接棒Space X和特斯拉,延续马斯克的科技财富神话。
但真正让Neuralink团队忍不住感慨“难以置信”的,或许是这个美好的叙事逻辑,在Neuralink成立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成立。
据媒体报道,在2022年到2023年初这段时间里,FDA多次拒绝了Neuralink的人体临床试验申请,并同时反馈了数十条必须解决的安全性问题,包括设备所使用的锂电池、植入过程中可能影响到大脑其他区域的线路材料、设备是否能够在不损伤大脑的情况下进行拆卸。
这种对安全性的反复强调也并不局限于技术层面。2022年底,有消息称Neuralink正在接受由美国农业部发起了一项调查,他们被指控在试验的过程中涉嫌违反“动物福利法”,造成了大量的不必要动物死亡。例如在2021年的一项试验中,总共60头实验猪里有25头猪因为植入了错误尺寸的设备而不得不执行安乐死——这件事虽然引起了Neuralink研究团队的警觉,据传2021年5月一名叫做Viktor Kharazia的研究员就曾经通过邮件提示团队“可能在FDA审查中带来风险”,但他们的决定是用36只羊重复了同样的试验,再次造成了羊的超额死亡——爆料消息的内部人士认为大部分的“动物惨案”是可以避免的,但马斯克总是不断催促项目加快进度,要求员工们“想象有一颗炸弹绑在头上”,否则“Neuralink的市场效应就要失灵”。
那时候如果仅从“脑机接口”赛道出发,单线程地观察马斯克,一个为了追逐科技创新而罔顾伦理的疯狂科学家形象跃然纸上。
更糟糕的是,马斯克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在马斯克的世界观里,人类变成“半机器人”将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事件,而要抓住这个风口,最现实的方案就是通过脑机接口完成和AI的整合,变成“人工智能共生体(AI symbiosis)”,也就必然要求更有效地方式来放大大脑皮层的EEG脑电信号。Neuralink选择侵入性脑机接口的的技术路线,“开脑洞”、在脊椎骨上打孔安装设备、在大脑皮层铺设线路,都可以看做围绕着这个思路的探索,这又决定了Neuralink必然会长时间地在技术、伦理两大雷区里来回碰壁。
以至于在2023年5月之前,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脑机接口已经在马斯克的创业版图里实质性地边缘化,每周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投入到了Space X和特斯拉上,分配给Neuralink的注意力可能还不到半天。
尤其是再把FDA人体试验许可当做脑机接口赛道的一个重要标志物,其实马斯克的脚步,还不如我们的一位老熟人,陈天桥。
著名失败者
关于陈天桥的“盛大败局”,创投江湖里流传着水面水下两个版本。
水面版本是2004年后接连发生几个事件让陈天桥对游戏业务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于是选择以“激进”的姿态推动盛大的业务转型,进而给盛大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试错成本”。比如从2005年开始,盛大以翻倍的工资从华为、微软等企业进行挖角近1100名工程师,斥资近20亿成为新浪最大股东,以全力打造盛大电视盒子,结果2006年广电总局一纸文件叫停了IPTV,整个业务瞬间没了方向。
还有2010年盛大的联合创始人、陈天桥的弟弟陈大年用来豪赌“手机互联网生态潜力”的盛大研究院。当时他百万年薪找来了“中国最好的300个开发人才”,从云存储、商业数据库、智能手机ROM到大数据、Web操作系统、云笔记,把几年后移动互联网所有孵化出过独角兽的赛道基本都开发了一遍,结果算得上出圈的产品只有“WiFi万能钥匙”。
科技自媒体人老编辑描写这段的时候,评语是“写出来都是悲剧”。
水下版本是陈天桥兄弟得了重病,对公司管理力不从心。陈天桥的官方解释是急性焦虑(panic attack)。他在2004年第一次发作,2009年经历了“失败的商业投资”后出现了第二次“更严重、更持久”的发作,发病的时候“压力很大,很痛苦……每天看到日落就觉得自己再也醒不过来”。所以才有了陈天桥两口子去新加坡养病的故事——按照陈天桥后来数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新加坡是一个能清静地“关注自身健康”又很“佛教”的地方,适合治愈这种涉及到心灵的顽疾。
陈大年也曾在一次采访中描述过这场病的严重程度,说是2008年5月的某天他忽然在浦东的罗山路立交桥底下发病,痛苦到产生了“真切的濒死体验”,只能望着立交桥上的车来车往一动不动地等救护车,再接下来的记忆就出现在了医院的急救室里,期间外界一度盛传“他和哥哥都走了”。那时候他才刚过30岁生日不到3天。
这件事至今都常被媒体们拿出来用来感叹创业维艰,或者用来解释陈天桥兄弟为什么选择在当打之年退居二线,安心当起了职业投资人。两个当事人也基本不反驳这点。
陈大年经常直言不讳地在公共场合表达出对那段回忆的“痛恨”,说自己在躺在桥下的那一刻顿悟了“如此玩命创业,根本是个错误”。陈天桥更是乐于承认自己“因为生病已经失去了世俗的欲望”。经典桥段是2014年盛大前脚刚准备从纳斯达克退市,后脚就有一家顶级PE就派人专程飞赴新加坡,力劝陈天桥选择在国内重新上市,并许诺陈天桥有机会“再次成为首富”,结果被直接拒绝。
而且值得细品的是,刊载了上述片段的《金融时报》没有透露该顶级PE到底是谁,记者也没有追问上市方案的细节,笔墨更多地用在了陈天桥“佛系”的气质上:“我31岁就当过首富了,为什么40岁了还要做这件事呢?”
那可是互联网批量造富、所有人大谈消费升级的几年,社交网络上还没有“佛系”这个说法,没多少人把“不争不抢”和“企业家品质”联系在一起。被公认低调、内敛的马化腾,2011年站在深圳威尼斯酒店门口教吴晓波下载微信,用“摇一摇”的功能互加好友的时候,都忍不住说了句中二感十足的“战斗结束了”,听得吴晓波直感叹“语调低沉、不容置疑”。
可想而知陈天桥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级别的“苦衷”。
佛与脑科学
但这段经历,“意外”地又成为了一个新故事的开头。
2016年12月,陈天桥和妻子雒芊芊带着一个宏伟的计划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他们宣布出资10亿美元成立一个全新的基金会Tianqiao & Chrissy Chen Institute (TCCI)以全力支持脑科学研究,并且已经对基金会款项有了初步安排——包括捐赠1.15亿美元给加州理工学院用于在校内建立天桥脑科学研究所,以及在美国寻找一块合适的区域建立一所专门研究“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的“陈氏大学”。
要知道根据《2015胡润百富榜》,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当时的资产大概是30亿美元(190亿人民币)左右。这意味着陈天桥夫妇一口气梭哈了三分之一的家产,砸向了一个半公益半科幻的事业。
这个纯纯大善人行为直接让创投圈炸了锅,媒体们开始集中讨论“陈天桥隐身的五年到底都做了什么”,然后又挖出了更多“猛料”。例如2015年11月盛大集团领投了以色列生命科技公司ElMindA,规模为2800万美元的C轮融资,以支持BNA(Brain Network Activation脑网络激活)系统的继续研究——BNA系统可以理解为一套用于测量和分析大脑功能的非侵入式解决方案,主要用于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脑震荡等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诊断——而如果以ElMindA作为模板进行检索,那么类似的融合虚拟现实技术与神经科学的科技公司,盛大集团可能已经投资了超过100个。
再比如盛大也对实体医疗表现出了别样热情。他们从2016年开始持续投资一个季度亏损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最大的社区连锁医疗品牌Community Health Systems(CHS),最终在2017年成为CHS的最大股东,一度持有超过22%的股权。
围观的群众们纷纷表示恍然大悟:原来以为陈天桥是高平陵之后的曹爽,计划着“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没想到其实是高平陵之前的司马懿,用“不持杯而饮,粥皆流出沾胸”来韬光养晦。
实际上陈天桥本人也没有直接否认脑科学研究的商业价值。2016年11月,他在SIXTH TONE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具体地谈到了自己对神经科学的期望:“作为一个商业企业,我们不排除脑科学的研究可能会带来真正的商机——例如,如果我们发现一种将记忆直接写入大脑的方法,那么将改变教育领域;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像《黑客帝国》那样规模的VR/AR世界,那么我们所熟知的娱乐业将不复存在……神经科学之所以如此诱人,部分原因在于它有可能制造下一个谷歌,或者甚至更大的公司。”
可TCCI的基因,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玄学。
按照陈天桥的说法,设立TCCI的灵感其实是急性焦虑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吃完药之后,他总会陷入一段“压力消失”“充满遐想”的兴奋期——而自己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就开始本能地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佛会发四十八大愿?为什么我们需要打坐、参禅这些仪式?同样的方法,为什么有的人容易入定,有的人容易走神呢?为什么有的人觉醒了,有的人不觉醒?
几年时间下来他想明白这样几件事情:
-如果把“空性”理解一种理想的大脑活动状态,那么打坐、入定、参禅就是实现这种状态的“技术”,高僧的苦修和悟道的本质就是“新技术研发”;
-所谓的“四十八愿”,更科学的解释应该是佛陀根据两千多年前人们的认知设计的实用方法,并且佛陀已经发现面对不同的大脑,需要有不同的方式来刺激对应的神经元;
-人类科技发展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和需求,而这种欲望和需求本质上是一种感知和认知。
所以今天TCCI虽然成为了生命科学领域里的一个标杆,被很多财经媒体反复计算估值。但陈天桥其实明确讲过,TCCI首先是“解决人类重要问题”的机构,是一个需要招募哲学家、神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宏观项目。其次是基石LP,计划投资40只处于早期阶段的技术型基金,放大找到下一个技术突破或下一个科学领袖的几率。甚至还计划在学校里修建一座寺庙,尝试帮助佛教更加“现代化”。
只不过在“解决问题”之前需要“发现问题”,需要神经科学家们作为起点从细胞和分子层面来理解大脑的运行机制。
实际的成果
也正因为TCCI这种复合型的出身,相比起死磕制造AI symbiosis的Neuralink,TCCI的成果更加多元。
理论层面,TCCI组建了一个由加州理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Richard Andersen带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参与的12人研究小组,尝试从后顶叶皮层的神经元提取前更清晰的运动信号——Richard Andersen小组已经发现,大脑的后顶叶皮层这个区域内存在意识的解剖学结构,其所释放的化学信号一部分用于控制眼睛运动,另一部分用于规划手臂运动。手臂运动区域中的动作计划以认知形式存在,指定预期运动的目标,而不是指向各个肌肉群的特定信号。
基于这个研究成果,TCCI首先在机械外骨骼领域迎来了突破。2013年4月,一位叫做Sorto的志愿者接受了脑机植入手术后,顺利地实现了仅凭“动动脑脑子”对转手腕、和研究生握手等机械手臂操作。一年之后,Andersen小组为机械手臂增加视觉算法,又帮助Sorto完成了“动动脑脑子就能喝啤酒”的复杂操作。
BBC Studios制作的纪录片《Minds Wide Open》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个场景,陈天桥兴奋地表示这是脑科学领域到2018年为止最激动人心的成就,甚至当场展示了另外一个试验——TCCI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David Anderson可以通过一个按钮来操纵小老鼠的情绪,一键躺平、一键暴怒——陈天桥说:“我们的大脑,强大到可以创造一个可以模仿声音和现实感的虚拟世界,这太不可思议了。”
临床方面,TCCI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周良辅医学发展基金联合成立的上海陈天桥国际脑疾病研究所,也是TCCI在临床领域里的一个主要阵地,旨在为大脑相关的疾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开发新的临床药物。
Synchron的微创植入式脑机接口 (BCI) 技术也得到了TCCI的重金支持。BCI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通过颈静脉微创手术实现脑机交互的技术,神经介入学专家奥克斯利博士有过一个形象地比喻:“血管是进入大脑的天然高速公路,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血管进入大脑的任何区域,不再像传统技术那样需要在相应位置切除颅骨”——这个思路能够有效降低脑机接口技术可能面临的“伦理”风险,同时也很适合脑机接口技术的“轻量化”应用。
比如Synchron的主打产品之一Stentrode,就是一个用来控制电子产品,旨在帮助病人们更好地与护理人员、家人朋友完成交流的小设备。
盛大在2021年6月参与了Synchron的B轮融资,当时Stentrode作为一项用于治疗瘫痪的突破性设备,已经在澳大利亚展开了临床试验,先期招募了4名瘫痪患者用来评估他们是否能在手术后,顺利地通过意识独立使用电子产品的能力,正需要更多的资金推动其在美国开展相同的临床试验。
2021年7月,Synchron正式拿到了美国FDA的试验许可。2022年6月,Synchron宣布首次在美国完成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2022年12月,他们顺利地获得了由比尔·盖茨个人基金Gates Frontier以及贝索斯的个人基金Bezos Expeditions领投、规模达到了7500万美元的C轮融资,盛大作为老股东也选择了跟投,Synchron的累计融资额达到了独角兽级别的1.45亿美元。
与之类似的还有盛大在2021年7月和红杉共同投资的脑虎科技。脑虎科技同样采用BCI技术实现所谓的“脑机接口”,并且旗帜鲜明地在Slogan在标明了他们相比于传统脑机接口技术的优势所在:是一家通过柔性脑机接口技术来保护及探索大脑的生命科技公司。
Synchron顺风顺水的故事里其实有个重要的细节。有好事的媒体希望陈天桥描述一下Synchron和Neuralink的技术路线差异,陈天桥非常明确地表达了看衰:“开脑洞对人脑的伤害是显然易见的……但由于马斯克对舆论的影响足够大,媒体和公众普遍忽略了对于病人的关注,还有技术手段对人的伤害……对脑疾患者来说,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仅仅适用于那些特别严重的神经系统受损患者,即完全瘫痪的病人;而对于大部分患者来说,需要安全性更高的非侵入或微侵入式脑机交互技术。相比之下,健康的人就更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在脑袋开个洞、再植入异物,没人愿意这样做。”
这句话本身无可厚非,但相比起2016年在SIXTH TONE专栏里强调“如果我们怀着摧毁其他公司的心态去研究神经科学,那么我们将在本该奇妙的发现之旅中饱受折磨”的陈天桥,这句话的风格更像是2007年之前的陈天桥。当时一篇标题为《整合者陈天桥》的文章认为“陈天桥、丁磊、马化腾”代表了中国创业者三种典型的气质,陈天桥用来指代“盛气凌人,你一抛砖,他就铺天盖地地侵略过来,非杀到老巢,把你说服,转变你的思维,否则不罢休”。
你看,陈天桥是不是悄悄地变回来了。
而且从最新的动态来看,陈天桥“复原”的幅度还不小。
5月11日,TCCI放出了一条高调的招聘信息,宣布将面向全球范围招聘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数学及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尤其看重拥有大规模语言模型经验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和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很多人结合陈天桥此前接受《第一财经》的采访,直呼“盛大盒子式”的抢人又回来了,原话是这样的:“中国有很多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才,有的被自动驾驶等行业高薪挖走,有的还在大学里默默做研究。我们希望能找到他们,邀请他们加入脑科学研究。”
还有一些“消息人士”匿名补充了细节。有人说陈天桥很早就在内部沟通里表示,“自己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很兴奋,现在已经到了发挥人工智能魔力的最佳时机”。有人透露陈天桥对ChatGPT到了沉迷的地步,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训练自己的大模型,还会邀请了数十位“世界顶级”的人工智能专家进行“无限制”谈话。
我作为一个外人,当然希望越热闹越好,更乐意见到陈天桥代表华人力量,和马斯克的Neuralink来一场真刀真枪的全面对抗。只是不知道被佛祖孵化过的TCCI,能不能适应这种“逐渐远离佛祖”的日子。